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域基础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日前发布。相较于之前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条例》具有更高的位阶和权威。
从《规定》到《条例》,内容上有哪些变化?生态环境部为何也被纳入督察对象?《条例》如何与其他党内法规形成治理合力?对此,《环境经济》专访了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孙佑海。

《条例》有六个方面的变化
环境经济:在您看来,从《规定》到《条例》,文件名称的变化能反映出什么?孙佑海:文件名称中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变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推动督察工作纵深发展、促进督察工作央地协同的高度重视。《规定》在内容上明显侧重于指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而《条例》对中央和省级督察统一调整,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作了更多规定。同时,文件名称中的“规定”变为“条例”,体现了督察工作逐步规范化。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2019修订)》第五条,“规定”仅能对党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的要求和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而“条例”能够对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关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作出全面规定。在《规定》的基础上,《条例》总结了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健全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体制机制,从组织领导和机构职责、督察对象和内容、工作程序和方式、督察整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形成“问题发现—压力传导—督察整改—成果运用—主动履责”的治理闭环。环境经济:具体到内容上,《条例》有哪些变化?孙佑海:我认为,有6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体现在督察权威性方面。为了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确保督察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条例》进一步坚持和加强了党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领导。就制定依据而言,《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制定。而《条例》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印发,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条例》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域基础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具有更高的位阶和权威,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就制度目的而言,《条例》第二条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纳入其中。就组织领导而言,《条例》第五条规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将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二是体现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为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体系,让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更有依据,《条例》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设作了更加全面的规定。与《规定》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主要内容且仅在附则部分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出有限规定相比,《条例》不仅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职责作出详细规定,还在规定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涵义与定位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关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负责机关、组织建设、督察内容、督察整改等方面的规定,有助于精准发现和解决地方的生态环境问题。三是体现在督察对象和内容方面。为了合理划分中央与省级督察的督察范围,推动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促进精准有效督察,《条例》对《规定》所规范的督察对象和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就督察对象而言,相较于《规定》,《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象不再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部门,并取消了“下沉到地方市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规定,新增了“生态环境部”这个督察对象。就督察内容而言,《条例》所规定的督察内容更加丰富,督察工作重点从治污转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体而言,《条例》第十四条不再使用“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以及整治情况”等表述,而是概括为“环境污染防治、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工作情况”,并将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改革任务的贯彻落实情况、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情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等纳入督察主要内容。四是体现在督察形式与督察程序方面。为了巩固督察制度成果,精准科学依法开展督察,《条例》丰富了督察形式,增加了有关制定督察问题底稿和审核督察报告的程序性规定。就督察形式而言,《条例》第十六条新增了“拍摄制作生态环境警示片”的规定,将针对重点流域、区域、领域、行业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专项督察,并拍摄制作生态环境警示片。此外,《条例》增加了对督察典型案例的规定,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对于例行督察期间发现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还应当形成典型案例并按照程序报批后公开。就督察程序而言,《条例》第二十一条对《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督察报告制度进行了延伸和补充,督察组应当对督察报告反映的问题制作问题底稿,同时成立独立审核组,对督察报告开展独立审核。五是体现在督察成果运用方面。为了增强督察整改的实际效果,精准有效开展追责问责,《条例》将“督察成果运用”单设一章。在整合《规定》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条例》新增一款,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将监督指导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开展追责问责工作,对重点责任追究问题进行督办,并设置了对追责问责不力情形的反向问责条款。六是体现在督察队伍建设和纪律责任方面。为了增强督察队伍的专业性,《条例》第三十六条对督察队伍的组成进行了细化,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人员、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相关机构人员、有关专家等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督察,并增加了关于建立督察人才库和专家库的要求。环境经济:您刚才提到,生态环境部被纳入督察对象,这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孙佑海:一方面,这彰显了党中央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生态环境部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条例》将生态环境部纳入督察对象,反映了党对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权的制约与监督,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作用,蕴含了“任何权力都不能游离于监督之外”的法治精神。另一方面,这为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统筹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部门,生态环境部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监管执法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督察制度通过对生态环境部在政策设计、监管执法、责任传导等关键环节的监督,能够精准揭示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生态环境部的整改带动全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确保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全链条畅通。
兼顾惩治性与激励性
环境经济:《条例》的一大亮点是把“督察成果运用”单设一章。在您看来,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孙佑海:这是加强追责问责的客观需要。该章设置了追责问责的有关规定,体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始终奔着问题去、奔着责任去,牢牢牵住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始终坚持严的基调、问题导向,层层传导责任和压力。这是完善生态环境治理闭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基本要求。该章设置了有关部门协调的工作机制,要求坚持部门协同,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检察机关作用,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移交机制。这为优化党政机关队伍建设提供了法定依据。该章要求将督察成果运用在干部管理中,明确将督察结果和督察整改工作有关情况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就具体内容而言,追责问责是本章的重点:一是明确问题线索的移交程序,确保责任认定的规范性;二是建立问责工作方案的上报机制,保证追责问责严肃、精准;三是设置对追责不力情形的反向问责条款。这一制度设计将督察整改成效与责任追究相联系,对整改不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单位和个人启动追责程序,能够有效破解生态环境问题反复、整改落实不到位等难题,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为了防止问责不力或问责泛化、简单化,《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追责问责工作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开展,并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监督指导,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对重点责任追究问题进行督办。对于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值得肯定的是,《条例》兼用惩治性与激励性手段,对于督察整改成效显著的,将形成正面案例进行宣传,发挥激励先进、交流工作、引领带动作用;对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中表现出色、成效显著的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将给予表彰和奖励。环境经济:您刚才提到,《条例》兼用惩治性与激励性手段。早在2015年,《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就规定,要将督察结果作为被督察对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规定》和《条例》均对这一规定进行了延续。十年来,您觉得在“惩”与“奖”方面运用得如何?孙佑海: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设以来,主管机关始终坚持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成果,对失职失责干部进行严肃问责。前两轮督察共移交667个责任追究问题,追责问责9699人,使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得到有效落实,对失职失责干部形成了强大震慑。当然,目前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对优秀干部的激励措施仍不够有力,缺乏明确的奖励机制和促进晋升通道。建议遵照《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制定明确的正向激励政策,对在生态环保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干部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如设立生态环保专项奖励,这样可以激励更多的干部积极主动地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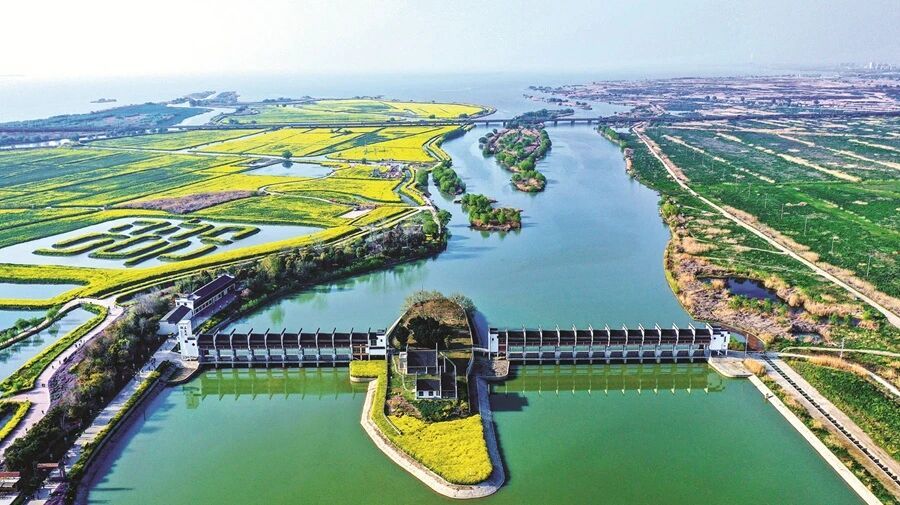
与其他党内法规形成治理合力
环境经济: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域基础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条例》如何与其他党内法规形成治理合力?孙佑海:作为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条例》与其他党内法规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形成了协同发力的格局,共同促进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和监督。在纪律处分方面,《条例》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形成合力。根据《条例》第三十一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监督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开展追责问责工作,对重点责任追究问题进行督办。根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对督察中发现涉嫌违纪的、督察组成员违反督察工作纪律的、被督察对象干扰督察工作的,将按照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处理。在干部管理方面,《条例》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形成合力。根据《条例》第三十二条,中央组织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督察结果和督察整改工作有关情况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加强督察结果在干部管理工作中的运用。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方面,《条例》与《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形成合力。根据《条例》第三十一条,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移交机制,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整改中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失职失责情况,督察组应当形成有关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线索清单和案卷,移交被督察对象,同时按照有关权限、程序和要求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廉政建设方面,《条例》与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形成合力。根据《条例》第三十七条,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严明政治纪律和相关规矩,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格落实各项廉政规定。在组织建设方面,《条例》与《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形成合力。根据《条例》第三十八条,督察组在督察进驻期间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临时党支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依规依纪依法有力开展督察工作。
环境经济杂志:https://mp.weixin.qq.com/s/b7a5CzpqOFOcgh5237S74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