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迎接130周年校庆,新闻网开设【百卅荣光】专栏,旨在展现天大130年来在办学探索、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光荣历程与历史贡献,将校史变迁和天大当下发展形成对照,传承兴学强国的校史文化血脉,振奋广大师生校友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斗志。本期我们来听方华灿老校友讲述天津解放前夕北洋大学的“学运”与“应变护校”。
天津市是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我1948年入学时正值天津解放前夕,我在北洋大学经历了解放前旧社会的峥嵘岁月, 目睹了解放后学校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 许多红色事迹,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8级学生入学初的“学运”
“学运”是解放前中共地下党领导开展的学生运动的简称。我是1948年考入北洋大学的新生,中共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领导我们1948级学生进行了“要公费、要面粉”的“学运”。
我一入学,就为进步氛围所感染。校园里化学馆的一层楼阅览室里的大桌子上有两个大玻璃框,一个框内是“辽沈战役形势图”,另一个是“淮海战役形势图”,我们课后常去这个阅览室,观看图上插的小红旗的变化。阅览室是学生自治会办的,插小红旗的人是地下党安排的,他们是在深夜里冒着“偷听敌台罪名”风险,收听解放区新华广播电台的战况报道后,去插的小红旗。校园里西大楼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内容有的是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丑恶,有的是声讨政府发行“金圆券”,剥夺人民财富的罪行等。北洋大学的北平师大附中校友会,还为我们新生中的校友召开了欢迎会,讲话的是何国模(1947年北平师大附中毕业,中共地下党员, 电机系学生),他向我们传播进步思想,号召我们新生要“组织起来”,向黑喑的国民党统治作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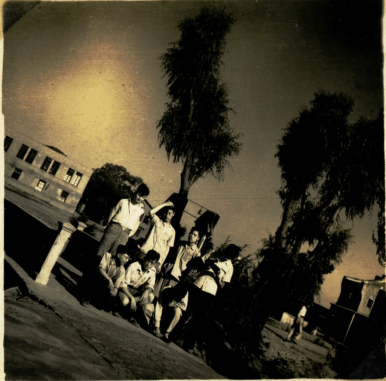
1949年6月底于北洋大学校园里北数学大楼前留影(后排左三为笔者)1948年9月初,一年级新生开始酝酿“组织起来”。当时,一年级男生全部住在四斋,它是由老图书馆的8个大阅览室改造成的8间大宿舍,每间住三、四十人。开初是由我的相邻房间里的印邦炎(理学院数学系,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发起的,他们串连其它7个房间的同学,准备成立“大学一年级学生联合会”,以向官方“要公费”。因为除少数同学入学考试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之外,其它同学无公费,所以大家都盼望能争取到公费,赞成“组织起来”。酝酿成熟后,于化学馆大阶梯教室召开了全年级学生大会,提名候选人,选举组成执行委员会。经投票选出了执行委员,余祚安(男,纺织系学生)为主席,我被选为执行委员。至此,1948级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联合会” 宣告成立。
开始,执委会代表全体一年级学生与校方交涉,向政府“要公费”,校方经请示政府后,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叫“公费”,只能叫“匪区”救济金。在地下党领导下,执委会表示不同意,几经交涉无果。于是,执委会研究决定,号召同学们“罢考”,都不参加月底进行的一年级学生的“会考”(当时一年级每月底进行一次统一命题集中两天的4门基础课的统一考试, 简称“会考”)。同学“罢考”后,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同意了学生的要求。
紧接着新问题又来了,发给学生的钱是“金圆券(国民党政府1948年发行的新币)”,它发行仅半年就已大幅贬值,同学们拿到钱,很快就贬值了,怎么办?经执委会研究,再次斗争,向政府“要面粉”,发给学生实物。有了面粉,既可向食堂交面粉入伙,又可存下来免受贬值之痛,同学们都赞成。几经执委会与官方交涉,政府担心学生再次“罢考”,迫于无奈,只能同意发面粉。至此,1948级学生的“要公费、要面粉”“学运”胜利成功。
天津解放前夕的“应变护校”
我1948年入学时,正值天津解放前夕。11月底,国民党天津守军进占北洋大学,在校园里构筑了炮兵阵地。学校被迫停课,学生在平、津有家的大部分回家了,留校的大部分学生疏散到市内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教室楼里暂住,很少数学生坚持留在校内,自愿参加护校。这时,在地下党领导下, 学生自治会组建了“应变护校委员会”,统筹西沽校园的护校工作和暂住女师学院同学们的生活活动。委员会主席是张恩桐(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 他直接与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启绍(杌械系三年级学生)单线联系。我被推选为应变护校委员会的“监事会”的监事。
应变护校委员会将自愿护校的几十位同学组成了护校队。护校队员们很辛苦,开始是搬运器材,将原来分散在教学楼、化学馆的一些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化学药剂等,搬运集中储存到楼底层地下室,护校队员们手抬、肩扛、背背,虽是冬天也常是大汗淋漓。护校队员除了做“搬运工”,还要做“更夫”,日以继夜地分批轮流巡逻及站岗,防止“趁火打劫”,保护校产。夜里巡逻的队员最辛苦,不仅在漆黑的冬夜里要抵御严寒,而且白天睡觉取暖,还要自已备燃料点燃煤炉(当时无暖气)。就这样,护校工作一直坚持到十二月下旬,直到大战即将打响,天津守军执意撵学生走,护校队才被迫离开舍不得的校园,迁至女师学院。他们迁来时,受到了热烈欢迎,同学们一致向他们的献身精神致敬。
这时,暂住女师学院的几百位同学,形成了一个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温暖大家庭。大家不分班级、系别混住在教室楼和体育馆的地板上“打地铺”。应变护校委员会组织了多种多样活动,丰富多彩,思想性强。如开辟的阅览室提供阅读进步书报,我就是在那里读完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的。
各个社团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十分活跃,北洋合唱团演出的几场“黄河大合唱”,激动人心,非常感人;男子篮球队竞然有时可以战胜“国体(国立天津体育专科学校)” 的校代表队;更令人刮日相看的是只有寥寥无几女学生的北洋大学女子篮球队,居然能与女师学院体育系的代表队一比高低,航空系四年级的女生王美英在篮球场上的巾帼英姿,令人难忘。晚间,北洋地下党支部组织了多个读书会,大家凑在一起交流阅读进步书刊的心得体会,我参加的是由北洋地下党党支部宣传委员魏兆民(冶金系二年级学生)主持的读书会,我们在昏暗的煤油灯及蜡烛光下(局部停电),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红色”读物。我就是通过这些启蒙教育, 逐步提高政治觉悟,后来,参加民青(地下党外围组织)的。
1949年新年初,突然在楼道里看到了以大字报贴出的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原来这是地下党安排党员在深夜里抄写张贴的,后来虽然天津守军、警、宪联合来大搜捕,但是在进步同学的掩护下,他们毫无所获。就这样,在地下党领导下,北洋大学学生团结一心,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接了天津市的解放,走上街头欢迎解放军,欢庆新中国的到来。(作者为北洋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52届校友)
